石英的红色情结
2024年03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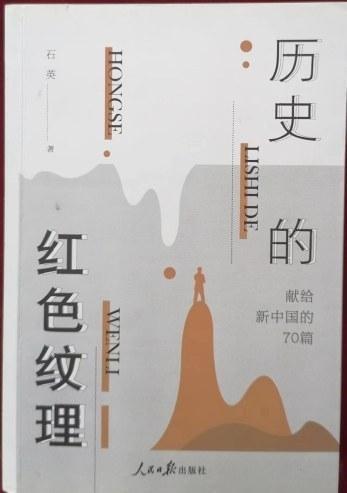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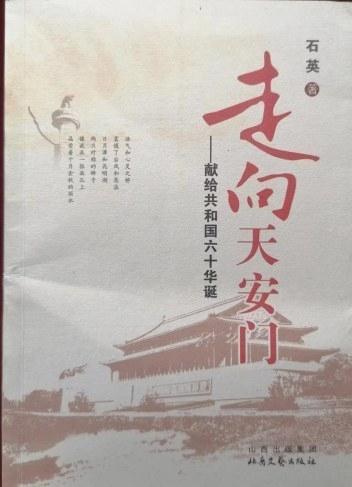
在当代作家中,石英是一个奇迹。
他创作甚丰,题材广泛,在上大学时即有中篇小说《文明地狱》、文学传记《吉鸿昌》等问世,素有“多栖作家”之称。如今已是九秩之年,依然佳作迭出,又被誉为“文学长青树”。迄今为止,主要从事编辑工作的石英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等各类作品总计70余部,1800余万字,平均每年20余万字,堪称“劳动模范”。
石英早期的作品我读得较少,对石英近十几年来的作品关注相对较多一些,且常常为他的作品所震撼、所感动。读这些作品,我发现一个现象,石英的作品中,常常浸润着浓浓的红色情结。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探索石英作品的冰山一角。
作为一个经历过那场血与火斗争的“红小鬼”,石英从骨子里对红色文化情有独钟,在他近十几年来的作品中,红色的篇章占了较大的比重。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夕,石英完成了诗集《走向天安门——献给共和国六十华诞》的创作。诗集涵盖了28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主要抒写了其中一些重要节点。自《1921,最热的日子》开始,至《十月的怀思》收尾,由72首短诗组成。每首短诗均独立成章,却又相互连接,彼此融合,描绘出新中国前进的足迹。
在这部诗集中,诗人主要选取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节点,或者是英雄人物,或者是革命事件,展开抒写,倾诉自己的仰慕、怀念之情。革命先烈矢志不渝的精神、大智大勇的品格、视死如归的气节、克服千难万险争取胜利的信念,贯穿全集。
3年后的201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石英红诗选》,诗集收录了作者新创作的短诗100首,分为“烽火硝烟”(历史事件)、“英烈千秋”(英雄人物)、“壮丽新程”(现实题材)三个部分,时间跨度大体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诗集以诗歌的形式再现我党、我军在不同时期的风雨历程,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景式描写独具特色。
作家出版社在这部诗集的封面勒口处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本诗集作者石英的生命‘基因’是:解放战争时期参与血与火斗争的‘红小鬼’;多年从事密码电报工作的机要兵;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士子;半个世纪中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的‘宿将’。这一切熔炼成为他持续不懈的追求,也才构成本诗集的思想与艺术、血肉和灵魂。”
201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石英散文集《历史的红色纹理——献给新中国的70篇》。全书分为“杨家岭的感觉”“将军的秘密”“过期的‘机密’”三个篇章。书中散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饱含深情抒写建党、建军、新中国成立相关纪念地和革命遗址的文章,如《闪光的征程》《井冈雕塑园》《“红都”感怀》《回眸雪山》等。
另一类文章则书写战争年代作者亲历的场景和事件,侧面反映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如《邂逅粟司令》《我所感受的“许司令”》《抗战岁月(九章)》《难忘胶东保卫战》《我在战争岁月中的几个“第一次”》等。
2022年11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了石英的散文集《伴随生命的记忆》,这部近300页的散文集分为“缅怀‘红色摇篮’往事”“印象里的抗日烽火” “革命的初心”等8个部分,共收录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73篇,如《童年的眼睛看抗战》《“苹果脸哥哥”和他的战友》《记一位“八路县长”》等。阅读这些文字,让人看到了一个“红小鬼”的初心和使命。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石英这样写道:“记忆是永恒的,是对过往足迹的珍重与对信仰的忠诚。这里所说的记忆包括笔者亲历的和铭记于心的。必须点明的是:笔者是生长于战争岁月的‘小鬼’和新中国成立前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本书中记叙的许多片段笔者都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本书稿的少部分篇章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和事,但也都浸染着一以贯之的红色基因,是红色血脉的延伸……成就此书,对我而言则是一种责任——朴素而庄重。我的理想是使我个人的记忆成为更多人的‘记忆’。”
读石英的这些红色篇章,我时常为作品中的红色魅力所感染。有评论这样评价《走向天安门》:“如果说小米加步枪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神话,无疑石英先生也创造了一个新诗的奇迹。” “可谓中国传统诗歌意境说与现代诗多面突破的成功融合。”
在创作手法上,诗人将某一段的革命故事浓缩于某一人物或场景之上,从历史、民族、人生等多个角度对人物或场景进行追忆、思念,让读者在这种多种视角的交织中去体会、感悟新中国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如《寻找井冈山》一诗,略去了极为艰苦而又惨烈的战争经过,诗句直抵“寻找”的深意和价值:“终于在黄洋界找到了俯视全国的/制高点;在茨坪的窗前/麻油灯和淡淡的墨香/映出八个毛体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诗性的表述,让我们对井冈山的认识突然深入了一层。好诗的抒情形象是大于思想的。这里的“寻找”,也是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寻找。“寻找”的哲理和诗意,对我们今天乃至将来都不会过时。
《石英红诗选》中,有许多令人惊叹的诗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从‘七一’到‘十一’/不过九十天的距离/但历史走了二十八年。”(《“七一”是这样的日子》)“今年一月当我走进小楼/我恍然看见会场里举起的手/每只手仿佛都是参天大树/合起来就是一片森林/这森林的覆盖面很大/后来绿化了整个中国。”(《遵义的选择》)“躯体跌进深山谷底/整个民气却随之升华/空谷回音:人死了,中国不死/枪折了,气节不折/五个人对五万万人是最小数/五万万有了五个才是真正的大数。”(《删不去的“狼牙山五壮士”》)诗集中这样的妙语警句迭出,耐人寻味。
散文集《历史的红色纹理》在谋篇布局和语言文字上也有着鲜明的特色。作者并不刻意追求谋篇之精巧,文章读来有一种“功到自然成”的驾轻就熟。也许与作者从事诗歌创作相关,这些散文的文字讲究,富含韵味,自然淳朴与诗化哲理相融合,读来感触颇深。在《闪光的征程》中,石英写道:“瑞金,这个赣南的不大不小的县份,在中国历史上多半是最小的‘都城’,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却拥有当时素质最为优良的人口,而且完成了一次果断的大迁徙——近10万军民甩掉妨碍前进的辎重——背负起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笔触从容不迫,情景交融,有韧性又有温度,不由得令人掩卷感叹。
在《伴随生命的记忆》一书开篇文章《心潮篇(二章)》中,作者分别写到上海和嘉兴两个重要的建党纪念地,在“上海,望志路那幢小楼”中,笔者写道:“后来的事实证明,从这里举步的路曲折而不平坦,然而正因为有了这惊人的第一步,黄洋界、娄山关、泸定桥和腊子口,纵然艰难亦能被后继者攀越……90年不仅是个吉利的整数,90年间的枪声织就了一个个无雨的黄昏和带露的早晨。”在“嘉兴,南湖那艘船”中,作者写道:“船,一直静静地停在那儿,是在向世人昭示:90年来多少度风吹浪打,它自泰然不动。初心不改,船与水共存相依,鱼和水永不分离。船似无人,人却无处不在……船在,人心就在。”这精短的抒情和富含哲理的语言,的确起到了提纲挈领之效,让人读后感慨不已。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石英作品中的红色情结绝非心血来潮,一时兴起,而是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社会意识,是他生命中的红色基因决定了他作品中的红色情结。
石英的革命经历可追溯至1946年深秋。当时,12岁的石英正读小学5年级,在班里担任学生会宣传委员。掖县(今莱州市)粉子山战斗打响后,12岁的石英作为“少年儿童宣传队”队员,随县里的支前队伍前往掖县粉子山支前。“我们这支少儿宣传队,两天来往返奔波,主要是慰问伤员和撤下来休整的部队,在炮声炸弹的爆炸声中为子弟兵唱歌、演小型活报剧,以鼓舞士气,受到了上级首长的夸奖和鼓励。”(《史地遗痕》)
1947年新年刚过,闻名胶东的大参军开始了。因为“年龄太小、个子又小”没有当上兵的石英,参加了由王县长任总指挥的黄县支前大队,作为这支支前大队中的“少年儿童宣传队”队员,石英参加了胶东保卫战、临朐南麻战役、莱芜战役,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体验了“战争中没有小孩”的残酷。石英不知道此次参加支前是不是王县长提的名,因为这时他已经参加了在解放区秘密组建中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
这一次支前演出,辗转数月,行程数百公里。在支前路上的小树林里,他亲耳聆听过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讲话。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我与首长和众乡亲依依惜别,踏上了漫长的(其实才300公里左右)返乡之路”(《史地遗痕》)。300公里在今天不过是几个小时的车程,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可是一个红色少年一步一个脚印走下来的。
一年后,这个“不穿军装的小兵终于成为穿军装的小兵”。这次是上级机关直接到石英所在中学选调译电员,14岁的石英光荣入伍,成为我军机要战线的一名“红小鬼”。
这一次,石英和几个伙伴从家乡出发,步行近3天到达胶东军区驻地莱阳。数十年后,石英还清晰地记得母亲为他送行的情景:“那是一个雪天,一场猛烈的大雪就像要把人埋起来,天和地都被雪针缝连到一起,母亲倒着小脚,不时地用手抹着被迷蒙了的眼睛。她大声嘱咐我:‘到了部队,早点捎封信回来’!啊!”“这一个‘啊’字,仿佛也被冰雪冻住了,变成一种恒久的天籁……”(《母亲以乡音送我参军》)
参军后,石英一直从事机要工作。在从事机要工作的几年间,石英曾两次打破机要译电新纪录,先后获得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司令部等机关的通令表扬,并荣立二等功。1952年9月,山东省团代会在济南珍珠泉礼堂召开,表彰了包括郝建秀在内的43名山东省模范团员,石英(当时名叫石恒基)名列其中,他同时被授予“模范机要工作者”称号。当时,参军5年的石英只有十八九岁,正是青春好年华。
行文及此,我倏然想起了《历史的红色纹理》一书中,有一篇《第一次看到“讲话”》的散文,写的是1945年春,石英在外村上高小,放学前校长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把一个密封的“牛皮纸卷”交给本村一位进步的音乐老师。中途遭遇伪军,因为他是“小孩”未被盘查而有惊无险。后来他才知道,校长让他转交的那个“牛皮纸卷”,是中共胶东区党委翻印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冥冥中,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便与那篇对中国革命文艺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讲话有了某种联系,这是偶然?还是必然?
也许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
注:孙为刚,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曾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已发表新闻和文学作品280余万字,出版个人专著10部,主编专著15部。报告文学《远洋渔歌》、散文《烟台的海》入选中学、小学语文教材。